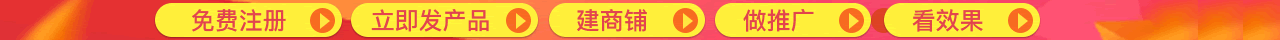参加“我们的声音”诗歌进工厂的诗人和嘉宾们 主办方供图
诗人郑小琼
郑小琼诗选
郑小琼的作品《女工记》
东莞时间网讯在中国作协会员、诗人彭争武看来,打工诗人这个群体所指的是离开家乡,出门谋生一族中写诗的,他作为其中一员,一路谋生,一路洗牌。“这个群体很容易产生思乡并对当下生存发展的感悟,容易用自己切身的体会,真实的感受,亲身的经验来创作,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一代农民工的生涯、内心的困顿、经历的沧桑。所以说在我们身上就会看到一个时代的发展史。”彭争武说,这个群体和诗歌作品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人口的变迁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文本,并因为这份见证证明了打工诗歌价值的永久性。
打工诗歌热潮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沿海城市,打工诗歌及打工诗人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了以郑小琼等为代表的一群诗人,也产生了诸多优秀作品,其影响甚至是世界性的,被许多国内外读者和学者喜欢。比如像郑小琼的《黄麻岭》《女工记》等,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她的诗歌被改编为国外的音乐剧,被一些博物馆收藏等等。
如今,随着时代进步、务工环境和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诗人们跳离“打工诗人”身份等原因,打工诗歌出现了“沉寂”现状。对于打工诗歌的未来,这是一个问题。
现状:时代文本与寂寥现实
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从上个世纪90年起形成一种热潮,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外来人口务工大市,更是集中了大量的打工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并形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成长在东莞的诗人郑小琼成为打工诗人的佼佼者和典型代表,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的范例。
当然,许多诗人和评论家都表示,近几年来,打工诗歌出现“沉寂”状态,一则是时代的进步,如今的务工环境是以前难以比拟的,因此没有以前诗人的那种强烈的生命体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曾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一个困惑的诗歌前辈,困惑于现在的年轻诗人无法表达他们那一代所经历的历史巨变的悲剧、苦难和困苦。
打工诗歌的“沉寂”还以许多诗人对“打工诗人”这个身份的逃离有关,认为这是个有着“污名化”的称呼或身份。许多当年的打工诗人如今也已从低端的打工阶层进入到“中产”,即便是诗歌创作在内容和题材上也大多跳离了原来的“现场”。用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诗刊》主编叶延滨的玩笑话讲,当年的打工诗人们都成了主编、主席、老总,完成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打工诗歌虽然也有一些优秀作品,出了一些优秀诗人,但在整个诗歌中只是占了很小一部分,即便在东莞这个诗歌大市,也只占了一个不起眼一个小角落。”柳冬妩说。柳冬妩是以研究打工诗歌理论研究起家的评论家,如今也已跳离“现场”多年,转向卡夫卡和清诗研究。前几年他出了本研究卡夫卡的著作,就有评论界的老师批评他:你研究卡夫卡,为什么还把它和打工文学联系起来,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逃离“打工文学”的机会。“这可能还是不忘初心吧,这种东西可能是精神上的胎记,没办法把它撕掉。”柳冬妩笑着说,对“打工诗歌”的所谓身份问题,他和许多诗人的心态可能有点矛盾。
诗人卢卫平也表示,打工诗歌,包括打工这个词,因为它有太深的时代烙印,他这么多年也想努力的摆脱这种打工诗人的身份,但别人仍然说打工诗人或者打工诗歌卢卫平。因为这个烙印,包括郑小琼,她的很多长诗,《玫瑰庄园》也好,虽然几乎跟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没有关系了,但是仍然作为广东打工诗歌的一面旗帜,或者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这是我们所谓广东诗人们的困惑。”卢卫平说。
世界性:全球化下的情感共鸣
目前,中国的打工诗歌颇受外国读者喜欢,甚至一些国外学者曾专门来研究中国的打工文学。对此,较早提出“打工诗歌的世界性”这个话题的柳冬妩表示,随着世界全球化、资本化、一体化的发展,未来不管是民族的还是地方的文学,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将呈现世界性,打工诗歌也一样。“打工诗歌所书写的内容和生命体验是与世界其他地方共通的。”柳冬妩说,中国的打工诗歌其实与世界文学也有一种互文关系。今天中国打工诗歌所呈现的工业化进程的现实与体验和狄更斯所言的那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的西方工业化时代类似的。
“外国读者中,年长的通过阅读中国打工诗歌会回忆他们国家曾经的年代,产生时代和人类命运的共鸣,年轻的则更多的是对中国打工者世界的好奇,通过打工诗歌文本窥探一个他们早已脱离的命运现场。”柳冬妩表示,工业时代的记忆基因和共同的文学审美,以及人文情怀,这是一种跨越语言、地域和年代的。
在打工诗人群体中,罗德远、谢湘南、郭金牛、郑小琼、许立志等三代打工诗人,以打工人+诗人的身份,不仅留下了大量广为人知的打工诗歌,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他们的主题基本上是怀乡村、流浪、孤独、身份缺失、异化劳动、受苦受难,所以他的情感大多是忧伤的、痛苦的、迷茫的、放落的。”诗人詹船海说,打工诗歌都在一种巨大的缺失背景进行对缺失的书写,这种缺失包括缺失故乡的归宿,包括缺失爱和关怀,包括缺失和谐的劳资关系,缺失一份满意的工作,以及缺失一个良好的定居制度。三代打工诗人以底层的身份留下了关于底层的史诗,在中国乡村的城市迁徙转变的过程中,记下了自己的切肤之痛,也带领着这个以农民工为主的群体的热烈诉求,留下时代的怀疑、批判和思考。
在研究中国打工诗歌或打工文学中,许多外国朋友会以郑小琼为典型案例。在郑小琼的诗歌中,东莞东坑镇黄麻岭这个她曾经打工的地方与钢铁一样成为其打工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意向。如今很多人还经常到黄麻岭去考察一下,看看郑小琼当年打工的五金厂还在不在,她写的凤凰大道还在不在。这对于一个地方来讲,它的文化意义也是不可预估的,它成为一个代名词和缩影,让世界读者了解的不仅是黄麻岭和东莞,甚至是中国沿海城市。
詹船海认为,郑小琼等一批优秀的打工诗人取得的成绩是全方位的,把工业题材和先锋诗歌的语言方式嫁接起来,从而使打工诗歌的品质更具有创造性,使文本更具有解读的广深度。因此需要以创世界的眼光,从历史的窗口来审视当前的伤痛与闪光并存的劳动,开启一种新的传统。“我们进入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大时代,大时代需要相应的大作品、大情怀,所以关于劳动创造的大诗篇,我们表现的主题将会宽广许多。” 詹船海说,这样中国的打工诗歌才能更具有世界性意义。
未来:超越生活之外去创作打工诗歌
打工诗歌为会怎样,大多数诗人和评论家都表示不太确定。但诗人谢湘南却做了一番特别遥远且科幻味道十足的猜想。他认为未来机器人将成为人类生活的深度参与者,时间域将刷新人类对万有引力的认知,人类在星际穿越、打工,地球将成为原乡。比如一方面为获得某种超能力,诗歌可能投入全新的味道,免疫于痛苦的感观。另一方面,未来智能时代人类的困境似乎并没有减少,打工诗歌也许会重申定义劳动。
当然,相对于谢湘南的科幻猜想,大部分诗人和评论家都从身边体验说起。何言宏认为郑小琼的《玫瑰庄园》写一个家族,实际上她深入了历史,对中国现代史的很多悲剧、灾难,都做了个体性的书写。“这一点从诗歌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何言宏说,打工诗歌的未来,应该以个体的精神立场去更广阔地关注打工生活之外的历史以及人类,在题材、诗意上面有更加丰富的扩展和表达。
面对打工诗歌存在粗糙、同质化的现象,诗人刘大程就认为,文本问题是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打工诗歌和其他文体一样,最终是要靠文本来说话的,像谢湘南和郑小琼等靠文本来说话的,并不是喜欢打工就出了诗歌。”刘大程说,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外部表象转向个人的命运去反映时代。因为现在的社会状况也是变化很多,不像打工初期、中期,那劳资纠纷一系列的矛盾非常尖锐,现在很多问题都可视化了,都是全面性的。
柳冬妩对打工诗歌的未来表示不清楚,甚至希望打工诗歌没有未来,最好消失掉。他认为打工诗歌见证的大多是底层打工者的艰辛和屈辱,甚至是残酷,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这种不好的体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制度的完善会逐渐减少,打工诗歌要么转变要么越来越沉寂,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