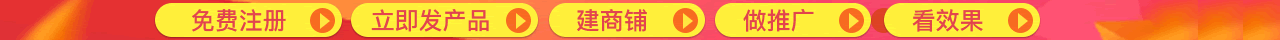妹妹陈苗得胃癌那年,才二十七岁。我正在家里绣十字绣,接到电话针就扎到指头上,然后整个脑子都木了,好半天才确认,我不是在做梦。
我大哭了一场。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丈夫罗伟业。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知道哭。
罗伟业在电话那端沉默半天,说,你取五千块,给陈苗送去吧!
我赶到医院时,陈苗躺在病床上,一脸死灰。见到了我,她的眼珠子才有了点活气。父母死得早,陈苗是我带大的。
后来陈苗离了婚,前夫是个二流子,只知道打牌赌博。离婚后还来纠缠过陈苗,找她借钱还赌债,还是我拎着菜刀,追着前妹夫赶了三条街,才把这个男人彻底赶出了妹妹的生活。
罗伟业曾经埋怨我多管闲事,人家两口子的事,你插什么手!我一句话就顶回去,照顾我妹,是我的责任!
这天我拉着陈苗的手,轻声说,别怕,有姐在。
陈苗说,姐,别管我。
我怎么能不管她?她都管了她半辈子了。
医生说,要趁着癌细胞没有扩散,尽早动手术。手术费是十万。
陈苗自己没有钱,她的房子是租的,之前在私营企业打工,一个月工资只有一千三。
我也没有钱,我和罗伟业都是国营厂的职工,吃不饱饿不死的,儿子正在念初三。
穷人最怕的事,就是生病。
回了家,我把家里的存折都找出来,在床上摊开,无论怎么加,都没有十万。只有两万五千块,那是给儿子上大学的钱。每个月存一点,每个月存一点,存得很辛苦。为了攒这钱,罗伟业上班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那样热的天,就在太阳底下走路,还对别人说,喜欢走路,可以健身。
我想了想,还是把钱全部拿了,其它的事,以后再说。
两万五千块全部交了陈苗的住院费,不交,医院就停药了。
我还试着把自己绣的十字绣拿给医院的病人和家属看,可人家只是看看,笑着不说话,当然更不买。
陈苗病情很不稳定,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疼痛让她情绪爆躁,抓着什么砸什么,有时候会向我吐口水,叫我滚。
陈苗说,你耗在我这里,班也不上了,钱也花光了,你还不如让我去死!
我一个耳光抽在陈苗脸上。妹妹二十七了,可我该打的时候,照样得打。
我说,你记着,你是我带大的,我对你有责任,你也要对得起我!
可是你对得起我吗?回了家,罗伟业像头暴怒的狮子,冲我怒吼。
我知道自己理亏,我宁愿罗伟业揍我一顿。儿子也站在父亲一边,还有两个月,他就要中考了,他憧憬的大学生活像画卷一般,却被母亲猝不及防地撕烂一个角。
儿子说,你连我上学的钱都拿,你还是不是我妈啊!
我羞愧难当,甚至不敢用陈苗的病情来为自己辩解,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是我,不能体会一颗当姐姐的心。
还是婆婆来解了围,婆婆说,陈苗是她的亲妹妹,这钱应该拿。
婆婆接下来说,可我丑话说在前头,这钱到这就止了,将来你妹妹要是病能好,是她的造化;要是不能好,也怪不到你什么了。
婆婆的意思很明显,我拿了两万五,已经仁至义尽,要还是继续填坑,就是我的不是了。
婆婆走后,罗伟业也冷静下来,他对我说,刚才是我的不对,那毕竟是你亲妹妹。可你不能只顾妹妹不顾家。你要想想,妹妹是你的亲人,我和儿子也是!
陈苗必须得动手术,医生否定了一切保守治疗的方案。虽然拿光了家里的积蓄,可那只是杯水车薪。
这天,我去找了陈苗的前夫,那个靠赌博为生的二流子,希望前妹夫看在曾经的夫妻情份上,帮妹妹一把。
我没想到,这次轮到前妹夫跟着我追了。那个刚好在牌桌上输红了眼的男人,顺手就操起院子里一根扫帚疙瘩,不分青红皂白地跳脚大骂:我们已经离了婚,她生病关我什么事!找后帐也没这么找的,你是不是看上我了?找借口来纠缠老子!
被罗伟业接回家,我忍不住大哭一场。罗伟业黑着脸坐在沙发上,等我哭完了,说,我说你就不能不折腾了吗?
那天我在街上无目的转悠,不知不觉就走到一条满是房屋中介公司的小街上。我心里一动,有点不敢往下想,但那顽固的念头,终于像毒蛇一样缠上了我。
我要卖房,罗伟业听见这个决定,像屁股上挨了谁的大头针,一下蹦得老高。
卖房?你真是疯了,那是咱们一家三口唯一的栖身之所,卖了去蹲桥洞吗?
我也知道这念头很荒唐,可我还是心虚气短地说,房子卖了将来再买,等大宝大学毕业,多少套房子都能给咱挣回来……
我没说完就被罗伟业暴怒地打断,你连他上大学的钱都拿走了,还指望儿子毕业了给你买房子!
罗伟业说,你这疯婆子,我要和你离婚!
我给陈苗梳头,她的脸已经瘦得凹下去,头发也掉了好多。
陈苗忽然说,姐咱出院吧!
我说,你闭嘴。
陈苗说,那天9床的老太太说,她认识一个人也是没钱治,就不治了,回去该吃吃该喝喝,没想到自己好了。
我鼻子一酸说,那是人家运气好,可咱不能冒这个险。
陈苗不敢跟我争,可到了晚上,我发现陈苗不见了,我疯了一般四处寻找,陈苗租的房子早已退掉,她能去哪里?
当我找到陈苗时,她已经在曾经打工的厂门口呆坐了好几个小时,像一捆枯萎的芦苇,奄奄一息。
我抱着陈苗,嚎啕大哭。
回到家,我跟罗伟业摊了牌,那就离婚吧!儿子愿意跟谁就跟谁,房子卖掉,一人一半。
罗伟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久久地不能发声,甚至不能呼吸。
就这么僵持一个晚上,天亮时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去厨房煮了一锅小米粥。粥咕嘟嘟地开了,我用勺子一下一下地搅着,连同自己的眼泪都搅进去。
我端着粥轻轻搁在罗伟业面前的茶几上。一抬眼,突然发现这一夜,只一夜,罗伟业的头发竟白了半边,看上去,就是一个小老头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跪下来,无助地抱住罗伟业的头,呜咽着,泪水奔涌而出。
罗伟业悲怆地回抱住了我,他说,疯婆子,房子要卖就卖吧,我不离婚,我和儿子认倒霉,跟着你去蹲桥洞!
房子挂到中介所两天后,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动手术的意义不大了。
我是怎么回到病房的,这个过程我完全不记得。当我有意识时,发现自己坐在陈苗床边。
陈苗笑了,她说,姐我不怕死,就是怕那边黑,找不着路。
我说,你从小就怕黑,记得有天晚上你一个人在家,忽然停电了,等我回家时,发现你蹲在门边哭,一摸都尿裤子了。
陈苗说,那次你把我揍了一顿,因为我把所有的裤子都洗了,第二天上学都没得换。
然后两个人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我的声音哽咽了。
我像哄孩子一样拍着她的背,陈苗说,姐我想回老家的房子去。
陈苗死于三周后。她在乡下老屋里,紧紧握着我的手,直到咽气都没有放开。
三周来,我陪她住在这老屋里,像小时候一样,每天给她梳辫子,给她煮野荠菜汤,搁点盐,味精,香油,再打个蛋花,是她小时候最向往的美食。
陈苗走的时候,我没有哭。所有的眼泪都在之前流光了,从此大约只有幸福才能让我哭出来。
幸福是什么?就是此刻远处那根烟卤,有袅袅的青烟冒出来,那是陈苗奔向天国的脚步。
幸福是身后这个男人,不富有不大方,却可以任我折腾,还有铁塔般坚实的身体,令我靠上去,幸福到眩晕。
我问罗伟业,你恨过我吗?
罗伟业说,恨过。但我想,你对妹妹有责任,我对你也有责任,你能做到不离不弃,我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