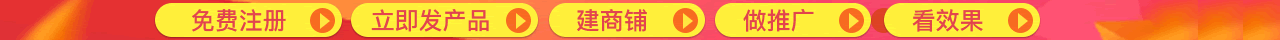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蒙古人民军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 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在“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